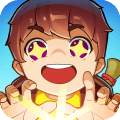《浮士德》主要讲了什么
2024-07-19 00:16:54作者:饭克斯
《浮士德》是歌德所著的悲剧作品。《浮士德》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关于浮士德个人遭遇的悲剧,而且是一部反映人类前途命运的史诗。
《天上序幕》的中心内容是上帝与魔鬼的赌赛。浮士德想从天上得到最美丽的星辰,要从地上得到最大的快乐,靡非斯特认为,这是怪诞的、愚蠢而又可笑的痴想。他表示他有十分的把握可以把浮士德引上歧路,使他放弃信仰,叫他象蛇一般地在地上匍匐而行。他就此要同上帝赌赛。上帝接受了魔鬼的挑战,并且也很有把握地说,在浮士德有生之年可以把他交给魔鬼,但浮士德最后绝不会落入魔鬼之手。上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敢于冒这样的风险呢?他知道,浮士德通过不断的追求定会走出迷津,找到他所渴求的真理。上帝有这样的信念是因为他懂得:人在努力时,总不免会走迷路,但是一个好人在他探索中总会找到正确的道路。同时他在这里还充分估计到了魔鬼在人类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他说:
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
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我因此才造出恶魔,
以激发人们的努力为能。
上帝的这些看法包含着深刻的意义。这里歌德对原来浮士德传说中的所谓“善”与“恶”的对立进行了彻底的改造。跟传说中不同,在这里“善”与“恶”并不是处于绝对的对立之中,而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两者相互依存,互相转化,又彼此斗争。所以人在努力时会走上迷途,在迷途中通过摸索又会找到正路。但更为重要的是,“恶”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破坏性的,它还是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人们的精神总易于弛靡,动辄贪爱绝对的安静”。
所以倘若没有“恶”的存在,人们就会停止前进。只是因为“善”与“恶”处于经常的对立斗争之中,人们才得以不断发展,不断前进。这是歌德对“善”与“恶”的一种辩证的看法。
歌德的这个思想在《浮士德》里就是通过上帝的形象表达出来的。
魔鬼的观点与上帝的观点完全不同。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都是固定不变的,不管浮士德如何努力,最后必然以毁灭告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帝和魔鬼并不是争论浮士德个人的命运,而是争论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在争论时是把浮士德看作人类的一个例子。当魔鬼大谈人世的苦难和人类的罪孽时,上帝没说别的,只是问他:你认识浮士德吗?在随后的争论中,上帝在重要的地方都只说“人”,而不提浮士德的名。
这就告诉我们,即将出场的悲剧主人公浮士德是人类的代表,他所经历的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他所追求的理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因此上帝与魔鬼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浮士德这个个人最后是否得救,而是人类的前途如何。人类到底是不断发展,还是日趋灭亡,它的前途究竟是光明还是黑暗,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全剧的主题。
《浮士德》这部诗剧所要回答的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第一次见到浮士德是在一个深夜。一盏昏暗的小灯,映出了一间狭窄的哥特式书房。这种气氛烘托出学者浮士德内心的苦闷。他正倚桌而坐,痛苦地回忆他的一生。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他读了无数的典籍,研究过所有的问题,但是现在依然是个“傻子”,一点真正的知识也没有学到。使他更为悲愤的是,长期的书斋生活使他脱离了大自然:
上天造了人放在生动的自然里面,
你却背弃了那儿的自然,
埋没在这儿的尘烟,
你和这些死骨相周旋。
他不想再去啃死的书本知识,而要认识活的自然。“我可再也不挥酸汗说那些我也不知道的东西;我要认识什么把世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我要看看万物的活力和起源,再也不玩弄辞令。”
抛弃死的书本知识,要求恢复人与大自然的本来联系,试图揭开宇宙的秘密,了解万物的起源,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要求,因而也是浮士德觉醒的标志。但是长期形成的积习,不易一下根除,因袭的重负还压抑着浮士德的心灵。就是在他以巨大的勇气抛弃了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僵死教条去探求宇宙根源的同时却又走上错误的老路。他不了解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也不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以为像过去一样,脱离社会,脱离现实,脱离实践,就能获得他所企求的知识。
于是他打开《大宇宙的符征》,想借此来认识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的原因。在这个符征中,他虽看到了自然现象和谐的联系,但这不过是好看的“幻景”!这使他大失所望,他呼喊道:“无穷的自然,在那里我能把你捉住?”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以为不经过实践单凭主观努力就可以一下子认识绝对真理。于是他召来了地祇,即大自然的象征,感到自己同它十分相近,并称自己是它的“同类”。但是地祇却回答说:“你相似的是你能了解的精灵,而不是我!”
地祇的回答说明浮士德在旧的道路上追求知识已经失败。这时浮士德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也正是在这时,他更加痛切地感到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他贪求知识的最大障碍。他知道自己置身于“错误的大海之中”,他周围的世界犹如牢笼,而他自己是其中的一名囚徒。他悲痛地想起布鲁诺、伽利略这些先驱者的遭遇,向那个罪恶的社会发出悲愤的控诉:
啊,说什么认识哟,认识!
谁个能呼唤小孩的真名?
古来有几位认识了点的人们,
他们都是大愚,不会明哲保身,
向着庸众披示了意见和感情,
已经遭受了谋杀和鼎镬的非刑。
在这个世界里得到真知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冲出禁锢他的牢笼,摆脱妨碍他求知的现实世界,以实现他了解宇宙的那种不可抑止的主观欲求,就成了他新的努力方向。他不顾可能“冲向虚无”的危险,为了“打通那条出路”,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自杀。他相信通过自杀,可以到达一个“纯洁活动的新的境界”,在那里可以实现他的追求。
因此浮士德自杀并不是象通常人们以为的那样,是因为他悲观绝望,走投无路,因而放弃追求,自我毁灭。浮士德的自杀是他那种为了认识真理,一切都在所不惜的主观奋斗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他坚持脱离现实、脱离实践的错误道路必然导致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浮士德决定自杀的时候,他的头脑中萌发出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认识,他说:
现在必须通过行动来证明,人的威力不亚于神。浮士德把自杀看作是一种“行动”,而且要通过这种“行动”来证明,人有能力实现他的要求。
尽管自杀这种行动对认识真理毫无价值,但浮士德终于意识到行动的意义,认识到行动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浮士德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因此打算自杀就成了浮士德在因袭的错误道路上继续向前的一个终点,也是使他朝着新的方向前进的一个起点。
当浮士德举起盛着毒药的杯子欲饮之际,响起了复活节的钟声,传来了天使的歌声。这在少年时代就熟悉的声音,使他想起自己走进书斋以前经历过的那种自然朴素生活的快乐情景。“昔日的追怀唤起我年幼时的情感,在这最后的,严肃的一步把我引回”。浮士德现在想起,在他所诅咒的现实社会中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还有实现他的要求的可能。一种美好的憧憬驱使他走出书斋,走向原野和森林。
复活节的早晨春光明媚,浮士德由瓦格纳陪同走过欢乐的人群,来到充满生机的田野。这里作者把浮士德和瓦格纳这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艺术形象放在一起,通过他们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感受和截然相反的态度来揭示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时代精神。
大自然的生机,人民的快乐,使浮士德无限感慨,他觉得这儿是“真正民间的天下”,只有在这儿,人才可以说“我是一个人”。瓦格纳对这一切不仅无动于衷,而且觉得人民的欢乐简直是“粗暴”,他们的歌声象着魔似的难听。浮士德看到大自然永不止息的运动,希望自己也能象小鸟似的立地飞升,在无边的天空自由翱翔。瓦格纳则表示,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他的精神快乐来自另一方面,即从书本到书本,从这章到那章。浮士德说他希望能有“一件魔术的外衣”,把他引向“海外的异邦”,预示他将借助魔鬼的力量走向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浮士德这一大胆的想法使瓦格纳惊恐万状,赶忙劝浮士德千万不要去惊动魔鬼,否则就会陷入灾难重重的境地。
浮士德和瓦格纳性格上的对立是多么鲜明。浮士德向往自然,热爱生活,瓦格纳脱离生活,仇视人民;浮士德追求真理,有远大抱负,敢想敢做,大胆无畏;瓦格纳一味追求僵死的教条和空洞的理论,前人没有说的话不敢说,前人没有做的事不敢做,鼠目寸光,谨小慎微。
总之浮士德要求打破中世纪的思想枷锁,冲出封建经院思想的牢笼,去探求新生活的道路,瓦格纳则竭力维护这个过时的思想体系,决心继续沿着现成的道路爬行。浮士德和瓦格纳的对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两种势力的斗争。浮士德代表了觉醒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感情、思想和要求,而瓦格纳则代表了落后、保守、反动的封建势力。浮士德站在历史前进的一边,瓦格纳站在反动的一边。
这两个曾是志同道合的老师和学生,由于对历史发展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而分道扬镳。瓦格纳随着历史的前进而销声匿迹,浮士德则跟着历史的步伐愈来愈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外出散步回来,浮士德又走进他长期国居的书斋。接触人民重返自然,固然使他深为快慰,但是他心中的烦恼并没有因此消除。他苦苦思索他那渴求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原因。
为了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拿出希伯来文的古本《新约圣经》,打算把它译成德文。头一句话就是:“泰初有道”。浮士德认为这句话不能照译,因为对“道”不能估价太高。他想到几种译法,都不能表达他的真实感情。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找到了一种说法,于是欣然落笔,译成“泰初有行”。“泰初有道”,还是“泰初有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说法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我们知道中世纪的教会和世俗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捏造了一整套所谓“理论”,并且把这些理论教条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永恒真理。他们强迫人们只准对这些“理论”作烦琐的推论,而不准人们从事有碍于这些理论的实践。新兴资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打破教条的统治,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就必须行动,因此实践对他们来说便成了一条重要原则。浮士德的这一改动,不仅表明了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而且也揭示了16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在思想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这也说明歌德本人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深刻理解。在这方面他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言论,例如靡非斯特说的“灰色是一切理论,只有生活的金树长春”这句话已经成了人们的座右铭。
从“泰初有道”过渡到“泰初有行”,这是浮士德思想上的一个伟大飞跃。现在他要“跳进时代的奔波,跃身进事变的车轮,不管痛苦和欢乐,失败和成功相互变换,大丈夫只是不停地行动”。他决心走向生活,通过行动来满足他的追求。这样他与魔鬼的订约就是势在必行。
正如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的那样,“假如追求着的浮士德不再进行纯精神的苦斗而转向‘实际生活’,他就不得不与魔鬼结盟。”这是为什么呢?生活本身充满了矛盾,它有许多陷阱;而任何一项行动的结局都有两种可能:成功或者失败,它所产生的后果也有两种: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这样浮士德要享受人生,从事实践,就给专门作恶的靡非斯特提供了施展其影响的可能。
关于靡非斯特和浮士德的关系,我们还须进一步加以分析。靡非斯特打算让浮士德充分地享受人生,得到生活中的一切乐趣。这对长期过着枯燥无味书斋生活的浮士德来说不仅必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的要求。
所以就这个意义来讲,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只是他们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本质的方面。对立才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实质。
浮士德所理解的生活并不是库非斯特所认为的那种低级庸俗的,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要求,浮士德把生活看作是他从事实践的场所。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浮士德并不象靡非斯特所认为的那样,把生活享受当作目的,而且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手段,看作是发展自己个性和认识现实的一种手段。正是在这些本质的方面,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我们说他们是对立的统一,他们订约是事物发展的必然,但他们又各有各的打算。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他们两个订约是由于浮士德在求死未成、求生不能时给魔鬼钻了空子。更不能说浮士德这么做是把自己出卖给魔鬼。歌德是完全从积极意义上去写浮士德与魔鬼订约的。
在歌德看来人类是在同各种恶势力的斗争中发展的,人类历史是在不断克服矛盾中前进的。浮士德离开了靡非斯特就不会有任何作为,没有靡非斯特,他也就没有了促使他前进的对立面。浮士德无论在“小世界”享受人生还是在“大世界”从事社会活动,靡非斯特都跟他影息相随,他的任何一项行动都离不开靡非斯特的帮助,即使象与海伦相会和改造自然这样的伟大行动也不例外。
因此浮士德与靡非斯特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歌德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关系,全面而又深刻地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兴起到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这个重要历史阶段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斗争。
悲剧第2部是第1部的继续和发展。它概括了从古希腊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近3000年的历史;它的背景从中世纪的德国移到了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又从那里回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主人公浮士德在第2部里进行了各种实践,经历了意义重大的发展。
悲剧第2部的写作手法也有不少独特之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严谨的故事情节,而是由许多形式上互不相关,内容上却是紧密相连的故事组成。这里作者运用了更多的比喻,采用了更多的神话故事,创造了更多的虚构场面。这样作者就有了更大的自由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述自己的见解,使这部作品反映出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
对于悲剧第2部的思想社会意义以及它的艺术价值,不少资产阶级学者提出过非议。费希尔武断地认为《浮士德》第2部是“不能理解的”,并写了一篇《浮士德悲剧第三部》来讽刺歌德的《浮士德》第2部。德国19世纪文学史家赫特纳认为:“《浮士德》第2部的艺术力量和艺术效果远不及第一部”,而且这主要不是因为作者年龄的关系,而是由于“题材的性质和对它的处理”造成的。按照赫特纳的意见,甚至第5幕“艺术上也是微不足道的”。这些论断是不能使人悦服的。
歌德在《浮士德》第2部里,不仅生动、具体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制度在德国的衰亡,揭露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矛盾,而且预见了人类历史本来的发展。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歌德在描写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时候,他没有象资产阶级自由派那样竭力掩饰和美化资本主义的矛盾,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人类历史最高的、最完美的发展;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把资本主义的矛盾如实地、赤裸裸地揭示出来,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更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另一方面歌德在揭露资本主义的矛盾的时候,并没有象反动的浪漫派那样是为封建制度唱挽歌,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的进步,企图退回到封建社会;相反,他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歌颂。
拿第2部的开头同第1部相比,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情景。时间不再是深夜,而是旭日东升的清晨;地点不再是令人窒息的书斋,而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原野。主人公浮士德也不再是倚坐桌旁心里充满忧虑和烦恼,而是身卧百花丛中逐渐苏醒。他感到生命的脉搏在跳动,心中产生了一种坚毅的决心:不断地向更高的存在飞跃。这截然相反的气氛和完全不同的心情,表明浮士德已经摆脱了中世纪加于他的沉重负担,他将以新的精神开始新的征程。
作者先把我们带到了封建德国的皇宫,从这个全国的政治中心,我们看到了德国社会的全貌。这种社会简直是个邪恶的世界,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皇帝形同虚设,诸侯小邦各自为政。反动统治者只顾寻欢作乐,挥霍浪费,结果国库空虚,民不聊生。抢劫和骚乱弥漫全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怒不可遏。
歌德在这里所描绘的德国社会的悲惨景象,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倒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死亡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
在这样的社会里,浮士德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为了实现他的理想,他就必须摈弃这个社会,走向另外的世界,这就是古希腊的神话世界。
歌德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尚未成熟,加之德国资产阶级十分软弱,所以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法国资产阶级那种通过夺取政权来实现他们理想的要求,而是象梅林所说的想在“文学里创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于是他们找到了希腊艺术,希腊神话世界。
在那里他们发现了美的理想,看到了一个纯洁的世界;那里的人自但是又和谐,并且享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们崇尚古希腊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实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
出于这样的认识,歌德让他的主人公离开了封建的德国来到了古希腊的神话世界。为了强调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及其代表海伦是进步人类追求的理想,作者特地写了一个饶有风趣的插曲。
在化装舞会上,皇帝出于享乐的目的要浮士德召来巴妮斯和海伦这两个美人。浮士德要靡非斯特帮忙,靡非斯特表示无能为力,他说:“你以为海伦是容易召来,象纸币妖魔一样?”并且承认自己与海伦“实在无缘”。这个刚才还在皇宫里大显神通的魔鬼,现在又变得如此无能,说明他与海伦的精神水火不容。
巴妮斯和海伦的幻影出现之后,宫廷里的人出于各自的动机,对他俩有的赞赏,有的挑剔。但不管是谁都把巴妮斯和海伦幻影的出现仅仅看作是一种惯常的游戏。至于巴妮斯和海伦的美和他们所代表的精神,这些宫廷里的高官显贵和皇妃贵妇是不愿也不能理解的。只有浮士德才真正懂得海伦的美和她的伟大精神。他一见海伦的幻影,就不顾一切地要捉住她。他感到只是在这时他才找到了立定脚跟的现实,于是他喊出:
她原在远处今已在咫尺,
我要救她她双倍地成为我的。
谁认识了她谁就不能同她分离。
浮士德要捉住海伦的幻影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招来了一场灾祸。但已经失去知觉的浮士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见到真正的海伦。何蒙古鲁土洞察浮士德的心思,于是在纯属虚构的古典瓦普几司之夜带领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来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
浮士德一落地,就“象安泰触地而生新力一样”。在这里他“预感到未来的福祉”,而且终于找到他久已向往的海伦。作者借浮士德与海伦的结合表明,那已经从中世纪解放出来的进步人类能够掌握希腊古典艺术。再联系到海伦在此以前一再遭受“苦难的厄运”,还说明古希腊的艺术只有被进步人类掌握才能获得新生。浮士德与海伦结合的直接结果是欧富良的出生。
根据大多数《浮士德》研究者的意见,欧富良指的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这是完全正确的。歌德确实很推崇拜伦,并且在《浮士德》里为他建立了一座丰碑。但是歌德塑造欧富良并非仅仅是为了纪念拜伦这位伟大诗人,更主要的是要表达他的理想,体现一种精神。歌德在1829年12月20日同爱克曼谈到赶车童子时说:“这就是欧富良!”爱克曼十分奇怪,为什么在第2部第1幕就出场的赶车童子,竟与第3幕才出生的欧富良是一个人呢?歌德解释道:“欧富良不是一个人,仅仅是一种比喻。……同一种精神后来可以是欧富良,现在则是赶车童子。这种精神象幽灵似的,无所不在,可以随时出现。”
那么欧富良所代表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歌德让他豪迈地
那么让我跳
那么让我飞
无论任何高处,
我都要冲上
这是我的憧憬。
他觉得他不能受任何限制,而且为了自由必须战斗;
祖国所产生的人们,
在危险里进进出出,
自由的勇气无限,
自己的血白流也心甘;
神圣的意志
属于不屈服的人,
一切的胜利
归诸战斗的人。
摆脱一切束缚,求得绝对自由,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并且为了实现自由必须勇敢无畏地战斗,这就是欧富良的精神。歌德正是在伟大诗人拜伦身上发现了这种精神,并且以拜伦为素材创造了欧富良这个艺术典型。歌德说过:“他既不是古典时代的,也不是浪漫时代的,他体现的是现时代。我所要求的就是他这种人。他具有一种永远感不到满足的性格和爱好斗争的倾向,……因此用在我的《海伦后》里很合适。”
在歌德笔下欧富良是古典美与浪漫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出现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当欧富良在音乐声中登场时,福尔基亚斯说:“听那些悦耳的声音,把古话赶快忘记干净;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请抛掉那班古老的神。”这个新时代已经不是以复兴古代艺术为中心的那个时代,而是随之而来的蓬勃兴起的资本主义时代。
如果说希腊神话世界的光芒驱散了中世纪鬼怪世界的阴云,那么现在人的现实世界又代替了希腊神话中的梦幻世界。这一切都是歌德人道主义思想的体现,同时也说明歌德热情歌颂古希腊的“美”仅仅是为了人的更高发展。
毫无疑问歌德对所谓欧富良精神是热情赞颂、倍加推崇的。但是他又认为这种精神,这种理想,远远超越了现实,因而无法实现。当欧富良觉得“荣名之路已开”,决心冲锋陷阵时,在幻觉中以为自己长出了翅膀,于是纵身飞跃,结果坠落在地,粉身碎骨而亡。欧富良遭到这样结局的原因是,他只求个人的自由离开了集体,他只是孤军奋战脱离了群众,他只凭主观意志不考虑客观的可能。那么在歌德看来,欧富良的伟大精神,伟大理想,如何才能实现呢?关于这一点,在悲剧第2部的最后部分作者作出了答复。
浮士德在遨游了古代神话世界之后,驾着海伦的衣裳化成的云彩又回到了现实的德国社会。从此开始了浮士德实现其理想的新阶段。
现在他不再是在主观的、艺术的虚幻世界里努力满足个人的渴求,而是要在改造客观的现实生活中,在社会实践中寻求真理,实现理想;现在激励他前进的不再是个人主观的要求,而是造福于他人的伟大事业。这是浮士德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取得的意义深远的重大进步。当靡非斯特要他当个统治者去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时,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并且说:
……
在这个地球上
还有余地做伟大的事业。
惊人的功业应该成就,
我感到我有力量担任。
浮士德所要完成的伟大事业是什么呢?那就是:围海造田,征服自然,发展生产。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面对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浮士德为什么不采取政治行动,而把征服自然,发展生产看作是一条理想之路呢?这样我们就需要简略地谈一谈歌德对法国革命和革命暴力的态度。象当时德国大多数进步作家一样,歌德对法国革命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但正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种热情是德国式的,它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而且只是对法国革命的理论表示的。”这就是说,这种热情主要是对法国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口号表示的。一旦革命从理论宣传发展成为革命的行动,成为流血的、暴力的行动,这种德国式的热情就变成“对革命的疯狂的憎恨了”。歌德并不反对法国革命本身,他对法国革命的社会和政治内容始终是充分肯定的,完全赞同的;但实现这个革命要用暴力他是反对的。歌德拥护变革,但这种变革不应是暴力的。歌德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歌德的思想中有许多辩证法的因素,但在对待革命,对待暴力的问题上他却完全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可见当时德国社会上的那种庸人习气是多么的浓厚,连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也摆脱不掉它的影响。
歌德对待革命的基本态度决定了浮士德不可能通过政治行动来实现他的追求。在歌德看来最理想的道路是,不必进行什么政治革命,就能实现变革,使社会前进。如果说过去他力图“在文学里创造资产阶级世界的理想图像”,那么现在则希望通过征服自然,发展生产来实现他的理想。
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这使歌德眼界大开,深受鼓舞,他热情赞颂这一伟大进步。当他得知开凿巴拿马运河的计划时,他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全人类都将由此得到无可估量的好处。他很想能看到这条运河的建成,他还希望建立一条连接莱茵河与多瑙河的运河和很快能建成苏伊士运河。
为了能亲眼看见这3件大事,他觉得再活几个50年也完全值得。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歌德看到了新的希望,他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而且会使许多政治问题获得解决。例如他曾对爱克曼说过,现有的公路和将要建筑的铁路会使德国统一。歌德对生产发展的歌颂以及他对生产发展所抱的希望,显然是从他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德国庸俗市民的立场出发的。
在他看来只要生产发展了,那就既可实现社会进步又不必实行暴力革命,这种想法是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他看不到生产力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之中发展的。当然他更不懂得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了。